|
|
 |
|
|
||||||||||||
|
| 您当前位置:农民互联网 >> 新闻频道 >> 炕头夜话 >> 说话说理 >> 浏览文章 |
|
难忘那段苦日子(十二) 无形的水,就是一匹野马,不服管束。要管束野马,就得有缰绳,要管束水,就得有堤防。堤防,是水的缰绳。文安洼是水乡,堤防到处都是,比较著名的有千里堤、秃尾巴堤、隔淀堤、防洪堤……
打堤,这是一种非常繁重的劳作,但细说起来,大体分两类,一是预防性地修堤、筑堤;二是抢险性地护堤。第一类与挖河一样,每年由决策机关制订计划,利用冬春两季,征用民工,开展施工。上世纪80年代以前,这类工程主要靠人海战术,铁锨、小车、土篮子,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人们手里逐渐有了钱,不少私人手里添置了挖土机、推土机、拖拉机,打堤也开始走向机械化了。比如,修筑环城防洪大堤时,每个乡镇都分派了具体堤段,有的乡镇手头紧,工地上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小车、铁锨、洋镐一起上,干得热火朝天;而有的乡镇有钱,工地上只有几台大型机械轰隆轰隆地响着,轻易看不到一个人影。 说起打堤的累,必须说护堤抢险。每年雨季,老天爷不高兴,多哭上几回鼻子,文安洼的老百姓就会忐忑不安,政府部门也会紧张起来。沿大清河堤岸上,一间间堤房会住上巡堤员,他们每隔几个小时就要沿着自己负责的堤段巡视一遍,看看会不会出现险情。假如出现决口,一场生死决战立刻会出现在眼前。文安的一位老副县长叫任谦益,是个老水利通,文安县的各个堤段有几道弯,有几个叉,有多少浪窝,有多少鼠洞,他都一清二楚。每到防汛期间,他是最忙的,哪里出现险情,准有他的身影。“共产党员,跟我跳!”他不止一次地这样喊着,带领人们跳入湍急的漩涡中,为堵决口的人们挡住巨浪,赢得胜利。 那时护堤,都要成立抢险队、打桩班,护堤抢险的办法也多种多样。有打桩,有援席,有挂柳,最普通的方法还是码草袋子。打桩,就是用四五米长的檩条,一棵挨一棵地砸进堤侧的泥土里,以增加大堤的坚固程度;援席就是用苇席挡住浪头的冲击,然后再填土堵住缺口;挂柳就是伐倒堤上的柳树,然后把树梢一头放到堤边水里,以减轻浪头对堤坡的冲击;码草袋子可能我们都看过南方抗洪的电视纪录片,我们这里与他们的用法一般无二。 如今,我们这里已经不是水乡了,河道干涸,庄稼缺水,好像再也受不着打堤这一累了。只是我们这里的地形没有变,老天爷还有没有下涝雨的时候?倘若有,还有没有人去受这样的累?还有没有人会干这样的活? 拔麦子
交芒种节,骄阳似火,西南风吹着一股股热浪,扑面而来。走进田野,麦浪滚滚,一片金黄,庄稼人打心眼里向外透着喜悦,啊,又是一个丰收年。然而,喜悦之余,也做好了吃大苦、受大累的准备。
说起庄稼人,祖祖辈辈过着苦日子。有句俗话说,庄稼人是土里刨食。其实,庄家人在土里刨的何止是食呀!先不说卖了粮食添置一家的穿用,就是一年四季做饭取暖用的柴草也都要从土里刨出。基于这个目的,庄稼人舍不得割麦子把麦根丢在地里,而是把麦子连根拔起,轧场前再把麦根铡下,为家里从夏到秋做饭之用。为了这点麦根,于是就有了四大累之一——拔麦子。 拔麦子是个累活,同时也是个技术活,一个拔麦子的好手,在地头一站,就能看得出来。来到自己的麦垄,左脚前,右脚后,塌下腰,左手从前面一揽,右手后面一合,往后一较劲,唰,一把拔下,一倒脚步,又一把,再一倒脚步,第三把,然后提起,在脚上把麦根上的泥土磕掉,捆好要,放在地上,接着又重复做。在部分农村,捆小麦的草绳被称作草要、草要子,也有的直接用两缕小麦打结来捆小麦,也叫要。 拔麦子累,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时间紧,容不得松半口气。俗话说,麦熟一晌,虎口夺粮。到了这个时节,天气说变就变,老天爷一发脾气,一场暴雨,再来几天阴天,老百姓的半年辛苦就会付之东流。第二,姿势单一,劳作时间长。拔麦子的姿势就是猫着腰用力,假如碰见水浇地,地皮板结,晒得结了痂,那就更惨了,拔不了几把,手上立即会出现几个大血泡。一天十几个小时,总是这样,到了晚上,最突出的感觉就是腰痛得直不起来,两腿痛得迈不开步。第三,工序多。拔、铡、晒、轧、扬,再晒、装,几道工序,要在最多一个星期内完成。 拔麦子虽是力气活,但也有许多讲究。到了地头,先排好顺序,谁挨着谁,谁和谁一趟要,这叫插夹垄。所谓一趟要,就是一个合作小组,前面一个人在拔麦子同时,要隔几步,用两缕麦子打一个结做成要,平放好,后面和他一趟夹垄的人则把自己和打要人拔的麦子捆好,这叫拾要。到了地头,还按照顺序翻个排好,这叫翻夹垄。 关于拔麦子,还有很多故事,大都说的是过去地主雇短工的事。因为我们这一带有一个习俗,主家在雇短工的同时,还雇一个领头人,叫掌作的(不知和《走西口》中“掌桌的”是不是一回事)。如果短工们能够超过这个掌作的,主家就会好吃好喝好待承,并且发给工钱,如果超不过去,只管一顿窝头咸菜,工钱一个不给。在浩然先生写的金光大道一书的开头,就有这样一个场景,张金发是个掌作的,一心想把一帮打短的穷哥们拉在后面,高大全使了个计策,在磕泥土时,故意往张金发脸上溅,最后,穷哥们都拿到了工钱。 时光匆匆,转眼之间,过去文安洼最普通的劳动形式已经成为过眼烟云了。科技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已经没有那么累了,在这个时候,我们重读古诗《悯农》,还有过去那样的感觉吗? 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 脱坯
文安洼有句俗话,说是一辈子不盖房,当个自在王。盖房,是农家一件大事,为了省钱,只有自己多受累。退回四五十年,农村的房子大概有以下几类:一、红砖大瓦房。除了公家能盖这样的房,老百姓几乎是不可能的;二、里生外熟的卧板房,就是里面用坯子,外面用砖,这样的房也是很少有人能盖得起的;三、挂斗房,就是里面用土坯,外面用砖,一层卧,一层立,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既省了砖,又增强了墙体表面的硬度;四、纯土坯房,而且还是老檐出头的。老百姓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来决定盖什么样的房。但是盖什么样的房,也免不了受这第四大累——脱坯。
盖房用的坯子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砖坯子。它的长宽高和砖窑里出的红砖一般大小,脱坯用的模子有一连三个的,也有一连两个的,脱坯者和好泥,在旁边放一堆细沙土,先在模子里撒一些沙土,然后扣掉,取泥放好摁实,用一个类似弓弦的工具,在坯模子上一刮,再把坯模子一扣,三个或者两个坯子便成功了。 第二种是大坯。它的尺寸大概是20×15×40公分,和文安古城的城砖大小差不多,坯子干透了也有20来斤重。脱这样的坯子要用滑秸泥,用的坯模子也是单个的,而且只是一个框。和好泥后,旁边要放一堆滑秸,用手挖起一块泥,放进模子里,再抓一把滑秸,往泥里摁,用手抹平,再提起模子,一个坯子就脱好了。 第三种是砸坯。这种方法不用和泥,但是要看土质。秋后初冬,在野外找个合适的地块,挖一个坑,取出潮乎乎的土,放进坯模子里,用墩子砸,砸实后,打开模子,一个坯子就成了。好像这种方法打坯子,不在四大累之内,但它也很有自己的特点,就是码放坯子。打坯者以自己打坯的点为圆心,按四五米的半径,把坯子码放成一个弧形,远远望去,坯摞犹如一个个碉堡,惹得小孩子们常常在其间玩打仗游戏。其实这样码放有一定的科学道理,首先离作业点距离相等,省工省力,其次凸面向北,减小了风阻,增强了稳固性,因为冬天多刮北风。 另外,过去不光是盖房要用坯,每年春天,不盖房的各家各户也要脱些坯,以备盘炕用。这是因为,老百姓家里睡的都是火炕,火炕都是用土坯盘的,经过一年的烟熏火燎,那些土坯都成了上好的农家肥,于是把炕扒了,把坯砸碎,运到地里,用新土坯重盘一个炕,就成了庄稼主每年必干的活。 脱坯的累,和拔麦子差不多,腰疼,腿酸。可是老百姓要盖房,还想省钱,不受这样的累,又有什么办法呢?那时盖三间房自己用小车推土垫庄基,自己脱坯,房顶用自家的秫秸,盖时乡亲们给助工,还要花一千多块呢,这是一家人多少年甚至是几代人的心血呀!如果你们家还保留着老房子,看看内层是不是土坯的,如果是,里面肯定浸透了你的父辈或者祖辈的汗水。 打草要子
□熊自洲(农民互联网湖北省网友)
草要子,是用稻草或麦秸编制而成的,一人多长,有别于草绳。要子,单股;草绳,双股。在我们南方水稻种植区,大都用稻草打要子,它比草绳粗,比纤子细,人们用它来捆稻把、捆麦把、捆柴把等,百把斤重的担子不在它的话下,用起来既省时又方便、环保,还可以重复使用。 草要子在农村是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每年冬天,生产队仓库里堆满了成捆成捆的草要子,一提提挂在屋梁上、水车下,一根根蜷缩在角落里。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家家户户都要打草要子,为来年的生产生活作准备。 草要子打法有多种,一个人用“要桩”打的要子,叫桩要。这种要子外形如缧丝状,上粗下细,打起来麻烦,但紧凑、结实、经久耐用,捆完麦把捆稻把,最后捆柴把。 小时候,见识了父亲给生产队打的桩要子。清早起床,父亲从稻场里挑回稻草,铺在堂屋里,喷上少量的水,用几条木凳压在稻草上,然后,从房间里拿出“要桩”(用碗口粗的木头自制而成,长250毫米,上粗下细,最上端有一80毫米长的细手柄)打要子,只见父亲坐在矮凳上,左手拉一把稻草,放在右手拇指上,拧成绳状,放在要桩下方,顺时钟方向“就”,边“就”边添加稻草,打到要桩上方,在凳子上一敲,抽出要桩,要子脱落,把要尾塞进要膛里,要子就形成了,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归拢。这种活,一般都是我来完成的,一担两个,十担一提,将要尾剩余的草扎成小辫,最末端搓成细绳子,最后打个死结,这样,要子才算完工。在我的记忆里,当时,每个社员每打120担要子,生产队就记一个工的工分,分值为10分。 闲得无聊时,我也拿起要桩,坐在父亲身边,像模像样地打起要子来,我打的要子不是粗了,就是细了,要么散了,父亲告诉我,打要子左手添草要均匀,右手应用力翻腕,千万不能把草直接缠在木桩上,我尝试过无数次,还是打不出有模有样的要子来,父亲鼓励我,等你长大了,有力气了,再来打吧,你一定能够打出好的要子来。 分田到户后,我开始像父亲那样打桩要,由于小时候掌握要领,加之手法运用得当,我真的打出要子来,虽不美观、光滑,但也能凑合着来用。 另一种是用“绞棍”绞成的要子。这种要子要靠两个人来完成,跟绞柴把一样,一个人站着边绞边向后退,另一个坐在稻草旁边放要子边添草,绞到一定长度,头尾合拢,自然拧成麻花状,一根要子结束。“绞棍”,就是用一根约2米长、大拇指粗的木棍,扭成180度弯,系上麻绳,在手柄上套上竹筒,像摇把。这种要子松散,不能重复使用,同样能捆麦把、稻把、柴把。 还有一种是用手打的要子。这种要子不用要桩,也不用绞棍,打起来简单、方便,无需俩人合作,就是直接在手上“挽”要子,形如鸡窝状,上口粗、底部尖,跟绞棍绞的要子一样不够结实,也属一次性要子,只能捆一些轻的秸秆、棉秆、稻草之类。 过去,草要子在农村用途广泛,除了捆农作物和柴草外,日常生活中也少不了它,农户的茅草屋,房前屋后柴堆、草堆上,横七竖八缠满草要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产队和农户打茅包(稻草包,用来储存粮食和种子),用的也是草要子。茅包的打法是,先在箩筐底部呈十字形放两根草要子,接着铺一层稻草,再把稻谷倒进去,封上口,扎紧草要子,退去箩筐,并横着缠上两根草要子,茅包就打成了,吊在房粱上,防止鼠害。 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农作物收割大都使用机械化,草要子的用途越来越小,也离我们越来越远。 “糊糊川”里喝糊糊
□刘春清(阳原县国土资源局) 早些年,阳原县农业生产条件差,土地瘠薄,干旱少雨,历史上素有“糊糊川”之称。人们为了生计纷纷到内蒙古“走西口”“走东口”。不信你到百度百科去查,一输阳原县,别名糊糊川,唉!穷名留下了,也传远了,不想让人知道都难。
有人说喝糊糊是当地地瘠民贫自然养成的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可不是,连3岁孩子都知道白面大米好吃,可不喝糊糊吃啥呀,没得吃,总不能眼巴巴地饿死吧。祖辈们自古就节俭惯了,无论歉年丰年,都是省吃俭用过日子,以防荒年。由于海拔高,气候冷,无霜期短,农作物每年仅收获一次,物产也比较单调,粗粮较多,主食多为谷、黍、豆、高粱、玉米。农忙时一日三餐为“早上粥、中午糕、黑夜糊糊煮山药”,农闲时多为两餐,即“早晨烫嘴(喝糊糊),中午难拿(搅拿糕),晚上歇牙(不吃饭)”。 过去,糊糊是把玉米或谷子在石碾上磨成面,搅入大铁锅水中,煮沸而成。也有以高粱面、黍子面、豆面来煮的,20世纪60年代后多用玉米面。就咱这岁数赶上了,每天早上睡得迷迷糊糊的,被母亲叫醒,在被窝里爬锅沿边拿长把铁勺搅糊糊。母亲一手拉风箱一手往土灶里填柴,我再瞌睡也不敢打马虎眼,一打盹锅里的糊糊就巴锅了,糊糊会更稀,舀在碗里能照见窗户档。鼻子影在糊糊碗里,还以为面疙瘩,筷子捞呀捞,老是夹不住,一抬头不见了,空欢喜一场。稀汤糊糊灌肚子,粗瓷大碗,三碗五碗地喝,尿上两泡,半晌肚里就咕咕叫了,糊糊实在不顶饥。“娘,我饿了!”成口头语了。 儿时总盼着有亲戚来,可人穷不走亲,连亲戚也很少走动。亲戚来了,就能喝上打米(放些小米)糊糊或糊糊煮山药(土豆)了。最难喝的要数杂交高粱糊糊了,生产队以粮为纲,就因杂交高粱产量高,全村不论水地旱地都逼着种上了杂交高粱,真可谓是田地山河一片红。可杂交高粱实在是太难吃了,酿出的酒都是苦的。杂交高粱面糊糊,别说难以下咽了,看看都厌烦饱了。那日子过得,吃没吃的穿没穿的,咋就熬过来了呢?一年四季一身衣,白土布用麻秆灰或锅底灰作染料,染成灰暗色。棉改夹、夹改单,甚至“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成年累月过着“衣不避寒”的日子。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行有车住有楼,吃穿不用愁,昔日聊以充饥的糊糊,对当地人的感情仍然如故,并对糊糊进行深加工,开发了系列糊糊面。有小米的、豆面的、咸味的、甜味的,进入了超市,还上了宾馆、饭店的餐桌。 两条惹眼的拉绳痕
□刘会强(平山县南甸镇北庄村) 7月30日我旅游回家后,因天气异常炎热,就打开了空调纳凉,并把身上的外衣脱去,也好尽情地享受这种清凉舒适的感觉。
在我脱掉外衣时,肩膀上的拉绳痕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因为这,多年来无论多么得酷热难耐,我都穿半袖体恤衫,从来不穿无袖的。拉绳痕像是一条在肩膀上游弋的蛇,总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那年我12岁,村里没有货车,也没有拖拉机、三轮车,连一辆牛车也没有。村民往农田拉粪或者收庄稼时,会用家里的板车。我家的板车又破又旧,一般力气较小的人拉不动,只有爹能够使用。那年夏天,爹在200里外的宅北乡打工,只有礼拜天或者节假日才能回家干农活。爹干的农活是家里的重体力活,比如拉粪。 8月初的一天中午,爹从单位赶回家,见家门口猪圈附近的猪粪还没有送到地里,就喊上正在午睡的我和弟弟,开始往农田里拉粪。因为我和弟弟第一次拉粪,所以都很兴奋,拽着拴在板车上的绳就往前跑,可走出去还没有一里地,就因天气炎热又累又渴受不了了,要不是被爹看得紧,我和弟弟一定会做逃兵。爹一边走一边给我们讲述拉车绳的要领,叮嘱我们要沉住气,不能一阵猛跑,那样不但做不出多少活来,还会累得够呛。 按照爹的叮嘱,我们将拉车绳套在肩膀上,可走了没多远肩膀就被绳勒出了一条深沟,又酸又疼,只好将绳放在另一个肩膀上,但不久也被勒出了一条又深又长的沟,加上天气炎热,汗水像掉珠子一样一个劲儿地滴……那一刻,爹教导了我们坚持就是胜利。晚上,熟睡中的我被一阵凉风吹醒,我发现爹正用一个破竹盖给我扇风纳凉。 那一刻,爹是那么温情,与白天拉粪时因为我们偷懒而吹胡子瞪眼的表情简直判若两人。也正是从那一刻起,我读懂了父爱。 难以下咽的花生皮炒面
□李同善(曲阳县东邸村乡西邸村) 中午放学后,孩子拿着一个鸡蛋送给我:“爷爷,熟鸡蛋,你尝尝。”我问:“这是从哪弄来的鸡蛋?”“我们学校每天每人发一根火腿,一袋牛奶,还有一个鸡蛋。”孙子把头一歪高兴地说。我接过鸡蛋,突然间回忆起小时候读书的日子。 上世纪50年代末,我读小学一二年级时,正是国家困难时期。一天放学回家,饿得我头昏眼花,看到父亲与生产队会计坐在桌前整理账目,桌边还放着刚用过的碗筷。我问父亲:“爹,你们吃的什么饭?我好饿。”父亲指着旁边的簸箕说:“你母亲才炒的花生皮炒面,还热乎哪,快吃吧。”我迟疑地拿起碗筷,抽泣着走到簸箕跟前,抓起几把涩涩巴巴的花生皮炒面,放在碗里,又舀了一点儿凉水倒上,用筷子慢慢地搅了又搅,拌了又拌,把炒面送进嘴里,嚼来嚼去总觉得垫牙涩巴,把脖子伸了几伸才免强咽下头一口。这东西虽说不好吃,但总能充饥。我央求在炕上做针线活的母亲做饭吃,母亲说:“米没有米,面没有面,柴禾又不多,我做什么饭?上学去吧。”我眼里噙着泪花,背上书包,无奈地又踏进了校门。 看看现在的孩子们,在家吃了白面馒头、大米饭和肉菜,党和政府怕孩子身体营养不好,还补贴营养餐,真是掉进了蜜罐里啊! (作者:佚名 编辑:admin)
文章热词:
上一篇:难忘那段苦日子(十一)下一篇:在农村,死人有地,活人没地,该怎么办?延伸阅读:
网友评论
以下是对 [难忘那段苦日子(十二)] 的评论,总共:0条评论
|
|
||||
| 农民互联网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授权不得复制或建立镜像 中国河北·惠农文化传播(石家庄)有限公司 办公QQ:2806279960 中国农民博客QQ群:213551375 业务电话:18233189910 Copyright 2013 nongmin.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冀ICP备13017983号 本网法律顾问:河北三言律师事务所律师杨永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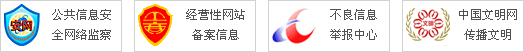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