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您当前位置:农民互联网 >> 新闻频道 >> 朝闻天下 >> 网罗三农 >> 浏览文章 |
|
高墙内外的“留守”——农民工二代犯罪调查原标题:高墙内外的“留守”——农民工二代犯罪调查 “没感觉”。 南方沿海某市的男子监狱车间办公室,门外是犯人们操作缝纫机的轧轧声浪,门内穿着工装的姚义秋按狱规坐在小板凳上,努力回想对襁褓中母亲出走的感受。 顿了一会儿,他又说:“会想她”。 隔着38年的时间,和从湖北乡下到滨海高墙内的遥远距离,姚义秋仍旧没有找到讲述童年情感的语言。就像20岁那年徒然的寻找:偶然听人说在大冶市街头看见了母亲,他和哑巴大哥一起赶去,辗转三天一无所获。 在这座南方监狱的高墙里,羁押着大量像姚义秋这样的犯人,他们入狱前的角色令人生畏:飞车党、抢劫犯、毒贩、人贩子、盗贼。再将视角前推,他们在或远或近的时光里,都曾经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留守(单亲)儿童。 国人开始注意到这个名词时,他们其实已经长大了,在各处角落挣扎求生,谋生的方式千差万别却又无例外地琐碎、卑下,没有闪光之处。 当他们偶尔在社会新闻栏目惊扰人们的目光,多是触犯了法律和人生的红线。而后他们进入高墙,开始了更长久的沉默。少有人的目光落到他们身上,张丹丹是例外。作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经济学者,她在过去两年以有留守儿童经历的服刑人员为对象,做了调查分析。她发现这些犯人在16岁之前有留守或单亲背景的比例相比于普通的农民工要高出一倍多,达到近20%。她的课题组设计了对多所监狱的调研方案,试图寻找出留守或单亲背景通向高墙轨迹上的线头和转折。 研究结果显示:留守或单亲背景,对犯人的暴力倾向、情绪不稳定性和感受不公平等方面,有着重要影响。这些人的生活轨迹粗粝凌乱,以致抛物线式的沉沦,或许从父母离家那天就已限定。需要强调的是,张丹丹和合作者在调研中,也曾试图研究农民工身份和犯罪的因果关系,结果发现,农民工身份并不是这些人犯罪的原因,而附加在这个群体上的人口学特征:如更加年轻,男性比例高,受教育程度偏低等,才是与犯罪相关的因素,这些因素放置于其他人群,可能也会得到较高的犯罪比例。而当在农民工群体和城市人口群体中抽调出同样的年龄、相同的受教育程度和性别,就会发现,农民工群体并不比城里人更容易犯罪。 持续城市化的背景下,中国的留守儿童数量仍在节节攀升,“留守儿童犯罪”问题也成为热门话题,但他们步入成年后的轨迹,仍旧处于晦暗中。 2015年9月,《凤凰周刊》记者和张丹丹一起走进高墙,见到了这些“身世特别”的服刑人员。 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抽出往事的线头并不容易。但那些人生经历的转折与死结,内心与外界的冲突和断裂,却是真实存在的,也只有在人生时钟被强制拨慢的高墙内,才有机会回顾打量。在冗长的服刑期后,他们走出高墙又重新没入人海,即使狱方也很难追踪到他们此后的行踪。 姚义秋们是大陆第一代留守儿童。透过高墙,一种无形的线索开始代际传递:姚和其他一些服刑人员的孩子正在遥远的乡村,重复他们童年的经历。 砖头和面具 邓晖的固执,一望可知,即使在这座“文明监狱”的炼炉内也没有化开。 他似乎从幼年起,一直在抗拒着什么,却连自己也说不明白。譬如对于父亲存殁的答案,监狱管教干部的信息是,邓晖的父亲在他两岁时坐牢,之后越狱失踪。而邓晖重复了两次的回答是:父亲在他生下来半年后死去,爷爷奶奶没有告知死因。 引起邓晖抗拒的可能是一句话,或一个词。一次,一个犯人小组长责骂了邓晖,邓晖一直暗暗忍到过春节,找机会用地上砖头拍了小组长的脑袋,让他缝了好几针。事后,邓晖被升为“严管”,会见时他的胳臂上带着标记。邓晖心情沉重,但“硬气”着不肯低头。在“硬气”背后,是他对自己的失望:“跟同改关系都不是太好,孤僻,容易发火。”邓晖盼望着早点出去,却又对自己获得减刑没信心。 “一块砖头”式的铤而走险,横亘于曾经的“留守儿童”和今天的囚徒身份之间。记者接触的十几位犯人中,年龄大多是“80后”或“90后”,罪案绝大多数和暴力相关: 邓晖,原为“飞车党”,在团伙抢劫作案中担任摩托车车手,发展了两位女孩入伙,判刑时被定为首犯; 姚义秋,伙同他人入室抢劫,用衣服蒙面,手持菜刀逼迫已上床入睡的受害者交出保险柜钥匙; 佘念武,和其他四名留守儿童背景的农民工结伙,拦路抢劫六次,打伤反抗的受害人; 崔凯,因为受同事欺负,手持红酒开瓶器捅瞎对方眼睛; 在张丹丹的调研中,抢劫和故意伤害是农民工最大宗的犯罪行为,高于民众印象深刻的强奸等罪行,经济类犯罪比例则很低。主要原因是:有留守或单亲背景的农民工犯罪群体受教育程度低,年纪更轻,在情绪不稳定、暴力倾向、不公平感等几方面都更严重,而在性格外向性、亲和度、负责任能力上都低于农民工群体的平均水平。这和他们童年生活在留守或单亲背景下,缺乏人性滋养和人际交往能力培养,人格塑造乃至受教育机会缺失有密切关系。在张丹丹课题组对这个人群发放的问卷调查中,51%的留守或单亲家庭的服刑人员表示:童年曾经对于父母不在身边感到不开心。 在入狱后的悔罪教育和心理矫正下,多数犯人看起来能顺利谈及自己的过去,以致对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个性缺陷的联系有某种认知,有人甚至可以侃侃而谈人生哲学。但这种在强制矫正和评分减刑体系下的反思,有时近乎另一种乐观的面具,他们内心的某些阴影并非真的就可以如此轻松面对。 对于参与入室抢劫的经历,姚义秋始终不愿接受自己是主犯,强调自己是“帮忙”,虽然是他拿刀胁迫已经睡下的受害者。而另一宗拐卖妇女出国卖淫的犯人吴金森,仍然觉得自己只是在表哥怂恿下“跟着玩玩”。 邓晖在“飞车党”中的角色是开车,“我技术好,摩托车后座可带4个人”。案发后主犯之一脱逃,被抓的邓晖作为主犯被判刑,入狱后他认为自己并未直接动手,一直想不通,“后来想,案子总要有个说法,认了”。实际上,邓晖被定为主犯的理由是,案子中两个从犯的女孩子,都是邓晖叫去入伙的。 很多犯人和家人真正的交流,是在进入高墙后开始的。他们童年时长年在外打工的父母对孩子步入牢狱内疚不已,而犯人们自己通常最感内疚的对象,却是抚养他们的祖父母。 邓晖和相依为命的祖父母感情很深,他之前在外打工时,会常给老人们打电话,听到邓晖的声音,老人们高兴不已,鼓励他在外面好好干。可“最终我令他们失望了”,这负疚成了邓晖在狱中沉重的精神压力。浙江台州人杨道德10岁之前也由爷爷奶奶抚养,他24岁是因抢劫入狱,父母只能瞒着年老多病的老人们,说杨道德刑期短很快就将出狱,而实际上还有五年半。杨道德不知道祖父母是否还等得到这一天。
更多人遇到的情形则是失望加上路途遥远,家人很少探视。 对他们来说,回归高墙外的社会,摆脱早年滑落的人生轨迹并不容易。学习特殊行业操作技能,是监狱为他们提供的职业准备,但在心理上,走出成长年代的“留守阴影”是他们沉重的课题。 一旦走出高墙,监狱很难获得他们的消息,“有联系的都是好的,坏的就没有下文”。再次获知情形,往往是几年后有人重新犯案,而且一般是回流到这座沿海城市犯罪,被重新抓进这座监狱。 这是高墙内的管教矫正体系无能为力的。 (作者:袁凌 编辑:admin)
文章热词:
延伸阅读:
网友评论
以下是对 [高墙内外的“留守”——农民工二代犯罪调查] 的评论,总共:0条评论
|
|
||||
| 农民互联网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授权不得复制或建立镜像 中国河北·惠农文化传播(石家庄)有限公司 办公QQ:2806279960 中国农民博客QQ群:213551375 业务电话:18233189910 Copyright 2013 nongmin.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冀ICP备13017983号 本网法律顾问:河北三言律师事务所律师杨永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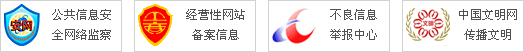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