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名片
- 姓名:孟燕君
- 性别:暂无
- 地区:暂无
- QQ号:暂无
- Email:78396900@qq.com
- 个人签名: 暂无
最近谁来看过我

oneoneone
状态:在线
admin
状态:离线
anchunchang
状态:离线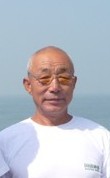
chunyu
状态:离线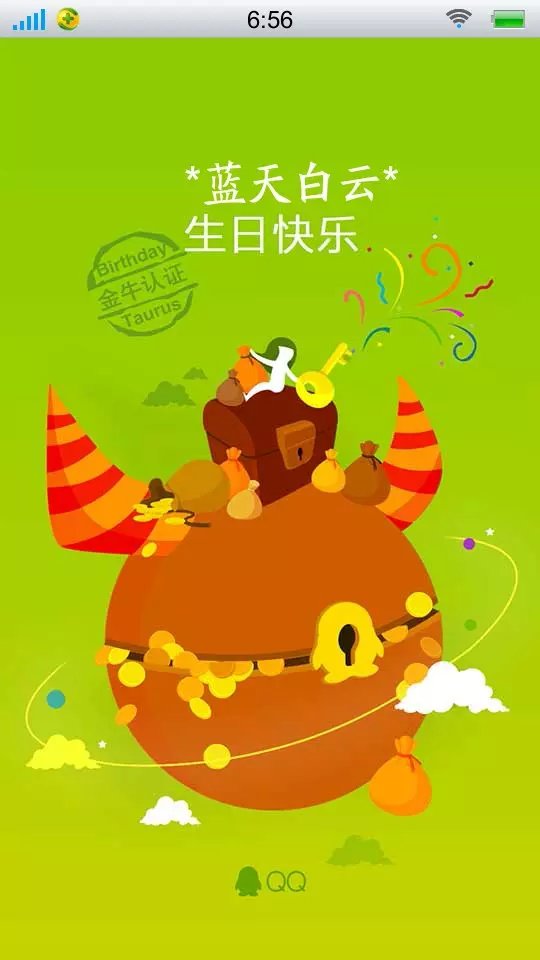
lanyun
状态:离线
liner
状态:离线
pugongying
状态:离线
usanh
状态:离线
bxgcdlxh
状态:离线
yuguozheng1234
状态:离线
博客统计
-
日志总数:1415 篇
回复总数:6458 条
留言总数:418 条
日志阅读:904228 人次
总访问数:3763066 人次
《趟出高粱地》:我的家庭[2007/5/13 18:48:00|by:mengyanjun] 

| 我的出生地座落在冀南平原上的临西县,虽然偏僻而普通,却有个诗一般的名字——马兰村。据志书记载:明代以前,原有万姓居此。明初,魏姓始祖由山西洪洞县诏迁至此,因祖上喜种马兰花,在村中植马兰花数株,取村名马兰。另据马兰村孟姓《孟子世家流寓支谱》载,孟姓由山东邹县迁来,先落居今临西县仓上村,明初迁居此村。孟氏62代祖宏升公,在原籍以贩马为业,明永乐年间,战火熄后,迁居此地,仍承祖业,渐至发达。后因孟姓人丁兴旺,别姓又尊重大思想家、教育家孟子,且旧时兄弟姐妹排行亦用孟、仲、叔、季为序,把孟称作老大,故取名孟家集。再后,孟姓、魏姓、李姓和睦相处,亲如一家,为淡化家族观念,因孟姓建有大规模马栏,为示纪念,取村名马栏,后族人共议,村名雅化为马兰。 说起我的家乡,就不能不提红高粱,因为我小时候天天喝高粱面粥,顿顿吃高粱面窝头。而说起红高粱,就不能不提那位曾红极一时的全国劳动模范、中共中央委员、女省委书记吕玉兰。1960年,当选为东留善固村党支部书记的吕玉兰,为了解决全村人的温饱问题,选择了较为高产的高粱进行大面积种植,经过5年的努力,人民生活条件终于有了初步改善。70年代初,吕玉兰走上临西县委书记的岗位,面对有人外出乞讨的贫困局面,她又号召全县大种高粱。 六七十年代的生产条件落后,土壤贫瘠,惟有高粱耐瘠薄、耐盐碱、易管理,旱涝都能保收成,但适口性差。有人就编了句顺口溜: “高粱窝窝难下咽,拔干拔的难大便。” 为了夸张,还有人说: “人吃高粱尿红泡,猪吃高粱不长膘。” 1972年9月,临西县在东留善固村召开高粱新品种推广现场会。会前,吕玉兰拿来几个红高粱面窝头,放在桌子上。几位县、社领导就大声议论起来: “这玩意儿就是好吃,白面馍馍也不如它!” 吕玉兰问当时在县医院工作的大会保健医生王大夫: “王大夫,你有什么看法?” “不好吃,这么涩,谁愿意吃它!”王大夫摇着头道。 吕玉兰站起来大声说: “听到没有,你们这些当干部的还不如一个医生敢讲真话!说实在的,我也不愿意吃高粱,可问题是有人连这个也不够吃的。等将来富裕了,咱谁也不吃高粱了!” 红高粱简直让我们吃腻味了,作为“又红又专”年代的红高粱,确实救了许多人的命。六七十年代我在村里经常看到擓篮要饭的人,但都不是我们临西县的。大种高粱时期的临西,和红旗漫卷、上下一片红的全国形势互相辉映,那真是红透了。在不产甘蔗的北方,惟一使我怀念的,是那种杂交多穗高粱和糖高粱的秫秸秆,比蜜还甜! 我的家庭,可以说世代务农,祖上几辈人都只会扛锄头、种庄稼,且生活贫困。爷爷虽然当过土干部,也只会念几个字。爷爷和奶奶就靠两间小西屋,为我的大爷、爹爹和叔叔娶了3房媳妇。那时人们的生活水平都不高,子女婚配不太注重财产,一是看出身,是地主富农,还是贫农下中农,二是看人性强不强。 1966年春,爹和娘结婚的第三天,就下起了毛毛细雨。春雨绵绵,把人浇了个透心凉。高粱秸铺成的房顶,一根像样儿的椽子都没有,嘀嘀嗒嗒漏起雨来,连睡觉的地方都保不住,爹娘只好头顶一块黑塑料布,在一个墙角处休息。结婚时借了一张桌子、两把椅子,第二天就还给了人家。当时因为没分家另过,锅碗瓢勺什么都没有。被面是自家织的土布,用红胶泥砸的颜色,还算新的,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里面的陈旧套子却不知用过多少年了。现在,洞房里就剩下夫妻俩、一床被子、一张破席和一个带豁子的盛高粱面的瓦缸了。 爷爷在3间正房土屋里住,他看看窗外的天,叹了口气对奶奶说: “二小(我爹行二,家乡人俗称二小——作者注)家不会闹事吧?” 奶奶说: “我去瞅瞅!” 奶奶披块头巾,来到西屋窗前,听到爹娘正在唱学习吕玉兰的歌曲《歌赞党的好支书》: 不怕风吹浪打, 不怕飞石走沙。 主席著作是指南, 广阔天地把根扎。 …… 于是,奶奶就乐不可支地去给爷爷汇报: “小金(这是我娘的小名,成立人民公社后起了大名叫夏明兰——作者注)不是爱富嫌穷的人,庆雨(我爹的大名——作者注)他俩弄不了事!” 当时,临西县刚由山东临清市划归河北省邢台地区,在离我们马兰村西南七八公里的下堡寺公社东留善固村,出了个了不起的全国女劳动模范吕玉兰,13岁读高小时就立下了改变家乡贫穷落后面貌的决心,14岁毕业回到村里,办起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岁就当上了村支书。吕玉兰能吃苦,敢拼命,干起活来像男子汉一样有力气,通过植树造林,平整土丘,终于锁住了风沙,粮棉产量逐年上升。 我爹在队里是劳动能手,别看个头儿不高,在海河治理工地上摔跤,三四个人也扳不倒他。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 “国家领导人中有个小个子,论起本领可都得服他!” 别人摇摇头说: “你怎么能跟邓小平比呢?大话大话!” 1958年,吕玉兰在西高尔庄村办起“红专”农业大学,我爹还是学校的优秀学生呢! 我娘的娘家是豆庄村,在马兰村南1公里地。娘姊妹10个,她是老大姐。因为人多负担重,没念一天书,从小就下地了。她是姚楼公社的劳动模范,也是“花木兰队”、“穆桂英排”的骨干,每年都能获得上级发给的奖状和铁锨、毛巾等奖品。 爹和娘结婚后,都表决心要向吕玉兰学习,争当先进,晚生孩子。这可急坏了奶奶和爷爷,他们想抱孙子,还以为我娘不能生育呢!因此,娘结婚两年后才生下我。 有人说我娘命苦,也有人说我爹不该打光棍儿。他们结婚没半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曾在抗战时期做地下工作,当村长时又得罪过几个地痞流氓的爷爷,被造反派打成了“黑特务”。于是,游街、揪斗、蹲牛棚,受尽了折磨。 在村民的记忆里,我爷爷是个党性特别强的好同志。他被打成右派,除了当村长刚正不阿,得罪了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民国时期,马兰村的大财主孟达三当了国民党临清县第九区区长,他人富心不黑,常常散财济贫,在当地老百姓中人缘颇好,堪称“及时雨”。爷爷在济南市供销社从事共产党地下工作时,孟达三已升为国民党军队的旅长,常驻泉城济南。二位好友交往多年,情深意厚,每每谈到国共两党不能并肩作战,创建中华伟业,就感慨万千,忧虑满怀。一天深夜,孟达三突然找到我爷爷说: “占魁(爷爷的化名,本名叫孟宪贵——作者注),我要跟随蒋总统去台湾,我实在舍不得你,干脆跟我走吧!” 爷爷斩钉截铁地拒绝说: “我是共产党,你是国民党,咱们走的不是一条道儿,你就死了那条心吧!” 孟达三哭了: “难道国民党不好吗?” 爷爷安慰他: “不是国民党不好,是国民党中的一些人和共产党闹分裂,挑起内战,屠杀共产党人和无辜群众,激起了民愤。你也是国民党,没做过什么坏事,老百姓还是称赞你的!” 这件事情,在济南党组织中传为美谈,人们都说我爷爷立场坚定,对党外人士的团结和稳定工作做得好。可历史的车轮滚到了1966年,爷爷和孟达三的那段交往史,却被个别人当成了小辫,揪住不放。 爷爷的“罪行”,株连到了全家。爷爷的子孙,便成了“黑特务”的后代。大爷曾被造反派摁倒在村南坑边的井台上,从那棵3个人都抱不过来的大柳树上砍下棍棒,然后蒙上大爷的眼,六七个人轮番抽打,茶碗口粗的柳棍就打断了3根。大爷被打得皮开肉绽,几乎别世。爹和叔被揪到群众大会上挨批斗,细铁丝拴着土坯,挂在脖子上,直勒得鲜血如注,也不能抬一下头、直一下腰。二姑家的大表哥立志从军,报效祖国,却被打得卧床数月。那时,如果家庭成分不好,人就不叫人了,被唤作“牛鬼蛇神”。 突然的变故,使娘觉得矮人三分,再也活泼不起来。有人劝娘跟爹离婚,有人给娘介绍了个当官的大龄青年,娘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娘是个坚强的人,她要用并不强壮的身体来承受这生活和精神双重的压力。 孩子毕竟是孩子,天性爱玩。就是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小小的我仍然玩出了许多—— |
标签:趟出高粱地 阅读次数(612) | 回复数(1) |
loading...
 加载中...
加载中... 给我留言
给我留言 加为好友
加为好友 发小纸条
发小纸条 小档案
小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