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姓名:潘修德
- 性别:男
- 地区:永年南桥
- QQ号:暂无
- Email:15632006951@163.com
- 个人签名: 暂无

oneoneone
状态:离线
miexuelei
状态:离线
yinheyishi
状态:离线
魏素英
状态:离线
admin
状态:离线
houlinhu
状态:离线
xiaojian
状态:离线
zhengxinmin
状态:离线
songshuming123
状态:离线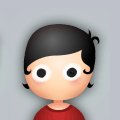
王志福
状态:离线
-
日志总数:712 篇
回复总数:2263 条
留言总数:27 条
日志阅读:297782 人次
总访问数:602020 人次
 我的童年是在旧社会度过的(一)[2018/12/15 18:16:49|by:panxiude]
我的童年是在旧社会度过的(一)[2018/12/15 18:16:49|by:panxiude] 
我的童年是在旧社会度过的(一) 当下举国上下都在庆祝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伟大胜利,我看了后很受感动。很多事情都是从建国后到1978年这段时期的经济发展来对比的,如果要跟旧社会比,即那又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现在我带大家一起走进我的童年----- 我的童年时期,正是日本侵略我国的时期,也是刚刚推翻二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建立民主政体才二三十年,大城市虽然有了一些民族的或买办的工商业,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的萌芽,社会形态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经济形态则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特点是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是自己生产自己用。基本没有商品贸易,所以更少货币流通。也就是人们手中没钱。我的童年经历和我看到的却是不能自给也不能自足的经济状况。 下面我从人们基本生活的吃、穿、住、行、用、生、死、医药、病等方面一一说说旧社会的真实情况。 首先说说 吃穿 民以食为天,在什么时候吃都是天大的事,没吃的就会饿死人。吃主要是吃粮食。我小的时候偏偏种地的就吃不了粮食。一是遭灾,收成小或绝收。二是日本人抢粮,土匪抢粮,一个村没有几家能全年有粮食吃的。所谓“糠菜半年粮”那是指的大户好人家。我家没有地种,全凭父亲推小车挣钱买粮吃,菜主要是野菜。没有买菜这一说。1943年,我家住在南关村,母亲就去五里之外的滏阳河沿岸各村拾白菜叶子和各种野菜叶子度过了一秋一冬。家家户户都不是顿顿吃饱,人人都是面黄肌瘦。住在南关的人,明知道河里苲草是大凉不能吃,吃了就拉稀,但还是有人去捞苲草。我也捞过,看着很嫩很干净,吃的时候还拉嗓子,吃了就拉肚子。只是咽的时候好像能叫肚子饱了,实际都是自己哄自己。真像唱戏的戏文所说:“河里苲草上称称。”那时要饭的乞丐特别多,都是没办法逼的。 吃菜用油炒,这是现在,那时就像南桥这个中等大村子,也没有几户用油炒菜的。油很少有卖的。农民都是把棉花籽去换油。有时有地的人家,在棉花不够苗时补种一些芝麻,收几斤换成香油,有一斤香油就很金贵了,那时人们常说什么什么贵如油,一切都可想而知了。丢几斤芝麻,等妇女生孩子时炒芝麻盐,这是好户人家才能做到的。 人们吃的菜,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吃饭时有菜的,没有菜咋办,就用自己种的辣椒当菜,因吃的多是粗粮,特别是吃高粮饭时,(我们这里是永年洼湿地,就只能种些耐水耐碱的高粮)难以下咽,这时辣椒就派上用场了,所以人们说,辣椒是“撵饭贼”。我常见三爷烧辣椒吃,吃的满头大汗。他说:“吃了辣的两头受罪----吃的时侯辣嘴,屙的时候屁股眼子疼,不吃还不行。” 我们这里沿滏阳河,种菜的比较多,大部分是大路菜当家,即萝卜、白菜最多。差不多每家都有一个小缸,腌各种咸菜,白菜根也不舍得扔,切成块放进腌菜缸,里面再放些老的嫩的辣椒。我吃时捡小辣子吃,不很辣,也能撵饭。 腌菜用的是“小盐”。“大盐”是海盐。没有,有也贵,农村没人用。小盐是农民自淋的。就是在下坡地里扫些碱土。在村边或自家大院用泥筑个长方形土台子,一头高,周边少高出三四指。低的一头插一束苇子,下面接桶,碱土倒在土台子上厚厚的一层,然后浇水,台子低的一头苇子下面的桶或盆子就会接到黄褐色的卤水,卤水经太阳晒或是用大锅熬,就会出现白色的结晶,这就是“小盐”,吃起来有苦涩味,有毒。大家都知道《白毛女》里杨白劳就是喝卤水死的,解放后为了人民健康,国家不叫用了。 在我童年的生活里,没听说过酱油这个词。这东西是有,叫“青酱”,可能城里有钱人或饭馆子用,老百姓家见不到。有酱,也是农家自己做的。原料最好的是黄豆黑豆,这是能吃饱饭的好户人家。差一些的是把平时吃剩的干粮收集起来,加盐和花椒面,磨成糊,发酵好了就是酱。自家做的酱是蛆的欢乐世界,吃酱时还得把蛆捡出来,没人恶心。常说:“井里蛤蟆酱里蛆”,习以为常了。我们家在解放前,饭都吃不饱,没做过酱,做酱是在1951年以后的事了。 生活中人们最不能缺的就是穿衣服了。我小时候夏天一般不穿衣服,七八岁的小孩在一起玩,就是一堆光屁股猴。少大些冬天穿的棉袄棉裤和大人们一样,就是只有棉袄、棉裤,这叫祼穿吧,不知道背心、裤衩、衬衣、衬裤、绒衣、毛裤是什么玩意儿。棉裤是圆筒腰,用长布条当腰带系住。我1961年当中学老师了还是穿这种裤子。西式棉裤家里人不会做,只能穿传统中式裤子,因为是祼穿,遇大风风就从裤腿一直钻到小肚子上了。人们想的办法是用绑腿带从脚脖把裤腿束住,所以大人都有绑腿带子。小孩就用个布条儿系住,暖和多了。小孩从二、三岁到十来岁,穿的棉袄两个袖子都有两片梗梆梆的明晃晃的东西,那是筻的鼻涕。 我们穿的鞋不认脚,不像现在分左右脚,穿上好看,得劲。那时都是大头鞋,随便穿哪只脚都行,当然谈不上好看了。有谁家小伙子穿上认脚鞋,别人都会眼气,那不光是穿家有面子,做家也会被看成手艺高强的好媳妇。我穿的棉鞋包不住脚后跟,年年冻脚。冻疮的血水沾住袜子,睡时脱不下来,钻心的疼,那时都冻脚。那时大人小孩一年都是只有两双鞋——夹鞋棉鞋。不像现在至少七双鞋——夏天有凉鞋,春秋有夹鞋,冬天有雪地靴,雨天有雨靴,室内有凉拖鞋、棉拖鞋,锻炼还有运动鞋。 由于大家都是穿的粗布(土布),不是机器织的洋布,所以不结实,成天干活的大人们,上衣、裤子都会被磨出窟窿,这就得补,可以绝对的说,没有一个人身上的衣服是没有补丁的。所以就有了“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说法,也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 我们小孩子们干活玩耍不停,就费鞋,大人来不及做,所以经常出现前边露着脚趾,后边露着脚后跟。即“前边露着五瓣蒜,后边露着大鸭蛋”,这 是太平常太普遍的现像。谁也不笑话谁。 由于都是农妇们自己织的布,都是白色,夏天穿白色还将就,秋冬就不能了,因为咱们这里白色是丧服,还得把白布变变颜色,大部分都是黑色或深蓝的藏青色。染色的染料有卖的,串村的货郎就有,染几丈布,用几两几钱的染料,再配两块石头样的臭电石,在开水锅里煮就行了。但是我家连买染料的钱也没有该咋办?1946年在冯堤村住,母亲和邻居们去村外找黄胶泥,她们把白布放到泥糊糊里揉搓,再去滏阳河边洗净泥糊,这样白布就成了淡淡的黄色,用这种布给父母做裤子。我们小孩子们穿的衣服是用另一种办法应付的。母亲叫我们去大堤上找“老鸹草”,把老鸹草的叶子夹在白布里用棒槌锤,那老鸹草的绿色叶脉就会印在布上,像花布一样。那叶子中间一根较粗的主脉,对称的向外放射出较细的叶脉,像半个雪花,能保持一段时间,近看好看,远看仍像白布。 平常干活,不讲究穿衣服的事,冬天为保暖,夏天为蔽体。没有条件追求更多的讲究,但是走亲戚就不行了。人们还是讲面子的,总不愿穿着破烂的衣裳去串亲戚,这就得借衣服。记着那是1947年我们去南马庄姐姐家赶会,爹还是借南邻家铁匠冯景的大夹袄和鞋。大夹袄是挂里子的长衫,一件顶两件,把裤子也挡住了,那时借衣服太普遍了。 我们家即使1947年“土改”后,仍是很贫穷的。被子少,不合一人一条,兄妹又多,只好“蹬脚”睡。就是一条被子睡两个人,翻个身都很难。个子大的常常能把脚伸到个子小的嘴上。直到1953年我上中学时还是这样。 总之 ,我和许多穷家的孩子们一样,吃穿都是很受罪的,特别是冬天,刮风下雪时,不敢出门。蜷缩在家里还浑身哆嗦。屋里没有火,只是做饭时有点热气。屋门后有个半截水缸,早起母亲做饭时还得砸开有一指厚的冰才能舀出水。我们兄妹都不愿起床,一直等母亲做好饭才不得不穿冰冷的棉袄棉裤,一个个嘴里都是嗤嗤吸着凉气身体打颤。最小的妹妹,母亲会照顾,把她们的棉袄、棉裤在火上烤烤,然后赶紧穿上。 未完待续 第二说说 住、行 那时的住房大部分是泥抹棚、土打墙,房高不过三米(九尺)。整个村庄没有几户是真砖到顶的大瓦房,就是当时认为是地主的大户人家住房还是砖挂皮,甚至有的还是表砖皮,内墙是用泥托的坯。 我父亲没有地,也没有房,记得是在南关街的北头路西租住着一座闭了门的旧店房,临街大门洞的套间里有个土炕,我们就住在那里,大门洞里盘了个烧柴禾的灶台,将就着住了两年。后来在老家的房后等老滩水落下后俺爹就用小木车往上推土,硬垫了二分地的宅基地,又推土垛墙,盖了两间坭抹棚。盖房的木料除了买的一架细梁外,其它都是老滩坑里长的一些没人要的野柳树和山椿柳树,粗的像大腿,细的像胳膊,搭好架子后,到好友地里帮忙干几天农活,从那里推几车高粱秸,铺到那些木头上,再往上加些苇叶子,然后上头遍泥,压几天瓷实了再上二遍泥。二遍泥不很干时就得上房踩跺一遍,把裂逢踩实,再到洼地里去找洼碱土,顶上铺了这种土就不漏了。 房顶不漏雨后,就可以收拾屋里了,先把房顶上下垂的高粱叶剪掉,再把土垛的毛墙泥一遍,这就成了我们的安乐窝。即使在1947年我们分了房子,那也是四间敞棚和三间泥抹棚西屋,但总比以前的好多了。 那时的代步工具就是铁脚大车,有钱的人家有所为的细车子,就是在大车上做做个木制的花格罩子,外面盖上花布,前边有帘子,人坐在里边,放下帘子外面就看不到里边的人,感觉很神秘。一般的大户人家就是套上一头牛,拉个大车,人坐在敞开的车里不用自己走就是很好的了。再下一等的就是俺爹推的小木车啦。他的小木车就是专门为别人推脚的,他那个行业就叫做”小脚行”。稍微有点钱的人家的女人们,要去走亲串友,还要讲点面子就顾用小木车推着走。再有一部分人家是自家养的小毛驴,说往那里去,骑上小毛驴走在路上也是觉得了不起。骑高头大马的是少数的少数,大部分是有身份的人,凡骑马者都有马童或随从,前后有人护卫。 洋车子(自行车)老百姓根本摸不着,所为洋车子就是外国造的,日本占领永年城,就能看到有人骑着前后打冲的两个轮子的铁管车子能行走,大人孩子很稀罕,一见到有人骑车到来,都互相召应围过来观看。汔车是日本人侵略中国时的一种运输工具,也能拉人,但是平民百姓是坐不上的。 旧社会的平民百姓走亲串友、赶集上会都是步行,没有什么代步工具。 第三说说 用 生产和生活用品百种千样,但绝大部分都是自己做自己用的。像生产的锄镰犁耙,都有农村作坊工匠小规模的生产。像辘轳栲栳都是传统手工艺来做,有些生活用品,如簸箩簸箕、荆耙、背筐、挎篓等都用荆条编成。还有苇编草编。像蒲扇,蒲扇在穷人的家中有八大用处——“当旱伞儿,当雨伞儿,屁股下边当垫儿,扇蚊子儿,扇蝇子儿,翻过来拍虫子儿,呼扇呼扇当风箱儿,放在盆上当盖儿。”它价钱又便宜,所以几乎家家有蒲扇,使用很普遍。俺娘就是编蒲扇高手,年年编,挣些零钱花。 那时我们做饭用的是砂锅,吃饭用的是黑粗瓷碗。瓦盆用来和面,洗脸 ,当便盆。用便盆在我家还算是讲究一点的,因为可以不出盖底窝,先尿到一个小小的瓦盆,然后倒在煤火台上一个大尿盆里。这是传承城里人的作派,还算“文明”。在南桥、韩屯、冯堤等等这些农村,人们都是屋当中放一个大茅罐,谁解手下炕去到茅罐跟前,很容易受风寒。没办法,习惯难改。 做饭烧柴禾,在农村不论冬夏百分之百没人用煤,我七、八岁时遇上灾荒年,穷到啥程度,说给现代人,可能有人不会信。比如做饭要点火,点火就是件大难事。爹在家时好办,他有吸旱烟用的“火镰”能点火。他不在家里时俺娘不会用火镰打火,就叫我去“引火”,什么是引火?就是拿一个用破布条烂棉花捲成一个大姆指粗的布卷,找有火源的邻家点着,回来吹着引着柴禾。找火源有时三家五家找不到,那时整个南关村也没有一家有洋火(火柴)的,有火源的家也是用旧布条搓成细绳,让它慢慢的着着。有的人家是用臭蒿编成的辫子,让它慢慢燃烧,用时用嘴吹着,生活就是这样过的。 生活是离不开水的。水是用来浇地,做饭,喝,洗衣,洗身子,洗头等。浇地,在南桥、韩屯等河边的村庄都用河水浇。挨滏河边,几户合伙打一眼透河井,用辘轳栲栳打水浇地。再往南一个村也没有一眼井,用地下水浇地是没希望的,都是“望天收”。吃水也是就地取材,每天早起都到有水井的地方排队挑水。在南关做饭喝水就是城河水,在南桥就是滏阳河水,这些水脏不脏,肯定脏。要不那时人得病特别多。我八、九岁时去下坡地割草拾柴火,渴的没法了,就手捧臭水沟里的水喝,烂鱼死蛤蟆漂在那,也顾不得了。听大人们说喝蝌蚪能治肚疼。潭路东边的水沟里有蝌蚪,我也喝过。捧一捧两三个、三四个一下就喝到肚里了,这就是那时的生活。 洗身子,我生长的南关也好,南桥也好,有河水,夏天洗个够。但冬天就只好忍了,一冬天不洗身子。有一年春天,天暖了,内热发生,我出汗了,好家伙,没想到全身的泥皴刷拉刷拉搓下来掉到地上一大片,少说也有二两重。 妇女洗头没有去污剂,连肥皂也没有。怎么办?她们很少洗,头发乱到一起就用木梳梳,冬天可常见到三五个妇女在北墙根成半天的梳头,由于洗头少,大部分头上生虱子。有人用洗衣服的“白土”洗,去不掉油污。有的头发乱了洗不开,就用麦麸子洗,当然不会有好效果。那时妇女的长头发也是让她们受罪的事。 我小时听大人说,夏天,有钱人没钱人一样过,这话不错,那时没有空调电扇,富人和穷人一样都是煽扇子。冬天是穷人受罪富人好过。这话也不错,因为富人可以烧煤取暖。我们穷人就不能。我除了每年冬天冻脚,还和别的小孩们一样手裂。没有护肤品润肤膏之类的东西。最好的护肤品是“蛤蚌油”,是在蛤蚌壳里装些油脂的东西。现在想可能是一些凡士林的东西,抹在手上防裂防冻管用,但不是经常有。洗手用的是“猪胰子”,的确是用猪的胰脏加碱捶练制成的,有去油污的作用,也不是经常有的。冬天,不论吃、穿、用,都是我最害怕过最受罪的时间,但又是躲不过的一个季节。 小孩子不管大人们如何的愁,如何的苦,我们还是寻开心尽情的玩耍。玩,没多少花样,简单的玩具都是自己做的。比如毽子、耳(尜)。那时男孩子玩的就那几样:打瓦、打耳、顶拐、踢毽,推铁圈;女孩子们玩的是抄绞、拿子、跳绳、打毛蛋等。有一次我见邻居的一只狗尾上长的毛特别长,很适合做毽子,我就和几个玩伴合作把狗用窝头引到街门缝挤住它,不能进不能退,后面的伙伴就用剪子把狗尾毛剪掉,做成毽子,又稳又好看,会招来很多玩伴来踢键子。 你们知道我们那时是咋的擦屁股的吗?我因为用字纸擦了一次屁股,被罚跪厕所门口几个小时。 事情是这样的,我虚岁七岁时,父亲望子成龙心切,虽然家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父亲还是决心把我送到城里教堂南边一座学校念书。整个南关村就我一个人。爹的信念是要想不叫孩子长大像他那样受苦,就得叫孩子们念书识字。他常像说书的那样给我讲唐朝罗成的故事。说罗成“七岁南学把书念,八岁丢文拉硬弓,九岁力劈山太子,十岁海走天下拜宾朋。”想叫我学罗成长大成大事业。那个学校好像很正规,入校还得对着塑像磕几个头,中间的可能是孔子。到西屋教室都是十来岁的小孩子,念《百家姓》。东屋和北屋听说是念《中庸》、《大学》的。到了那种环境,我感到高兴,兴奋,好像进入了“文明世界”“文明殿堂”。大家穿得很整齐,(母亲也给我换了没补丁的衣服。)见了老师都规规矩矩的鞠躬。好新奇好新鲜啊。特别是厕所里同学们解大手,都是用纸擦屁股,就是和我们农村的野孩子不一样。我就自觉的向他们学习,向他们看齐。我回到家里翻箱倒柜的找纸用来擦屁股。还好,我找到一本麻头纸的旧账本,就撕下几张带在身上准备到学校擦屁股用。当我骄傲地记事以来第一次用纸擦屁股不到几分钟,我就大祸临头了——有人在老师那里告我状了,说我用“字纸”擦了屁股,犯校规了。那个五十多岁穿长衫的先生把我叫到讲堂桌前叫我伸手要打板子,我不伸手,不是反抗,而是害怕。听说打板子能把手打肿,非常疼。先生说了几次我没伸手。他急了,叫两个大点的同学把我拽到厕所门口跪下。我根本不知道错在哪了。我学着同学们用纸擦屁股是我的一大进步和提高呀,怎么反而罚我下跪?我满肚子委屈在那跪着哭。后来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一个先生从那里过叫我回去了,回教室先生见了大声嚷:“怎么回来了?”有同学说是校长叫回来的。还说:“他没给校长鞠躬。”又告了我一状。但这次先生没说话,我算过了这一关。但我不知为什么要罚我,临下学时我的同姓叔潘清海指着厕所墙上写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敬惜字纸”四个大字。他说:“字就是孔圣人。不能用有字的纸擦屁股,该罚你。”我这才知道我们这穷孩子是注定上不起学的。我们穷得连饭都吃不饱,哪还有钱买擦屁股纸。我们是进不了那个社会阶层的。满肚子委屈回家不敢给爹娘说。好歹没过几天我就不上学了。那是民国三十二年大灾荒,加上日本鬼子疯狂的掠夺,人民没法过了,学校也散了。我家也需要我拾柴火做饭用了。这次上学我背了半页《百家姓》。当了两个月孔圣人的弟子,罚跪厕所门口。这是我第一次上学的经历。 我们农村孩子是怎么擦屁股的?样式可多了。在家里解完大手,最多的是找块小砖头,不带锐角带钝角的,用它擦屁股。有时找不到合适的砖块,就会在厕所墙的墙角,蹶起屁股在墙角蹭净。在地里割草拾柴时擦屁股的材料就多了,主要是植物的叶子,像棉花叶、豆子叶,猪耳朵草,茄子叶、烟叶等,最好的是大麻籽叶和麻叶,又大又软和。北瓜叶黄瓜叶有毛刺不能用。在下坡地割草就好办了,到处是水,用水洗,干干净净,十分惬意。大人们在地里干活擦屁股有绝纱的办法,你猜是什么办法?——脱下来一只鞋,用鞋底擦屁股。谁的专利不知道。这个发明很好使,没有开会上报纸推广就普及了半个中国。 未完待续 |
标签:panxiude 阅读次数(557) | 回复数(7) |
 加载中...
加载中... 给我留言
给我留言 加为好友
加为好友 发小纸条
发小纸条 小档案
小档案